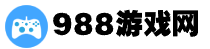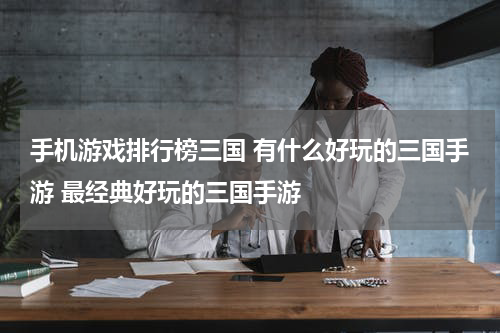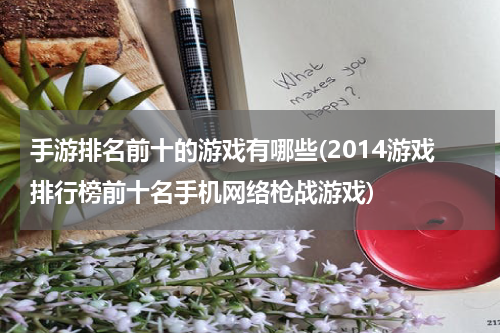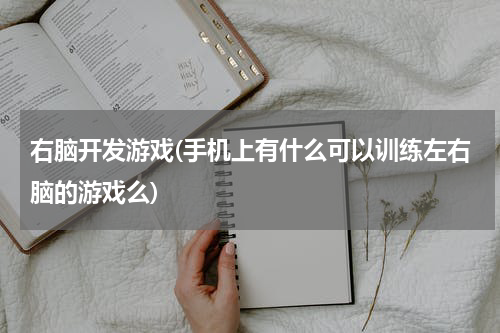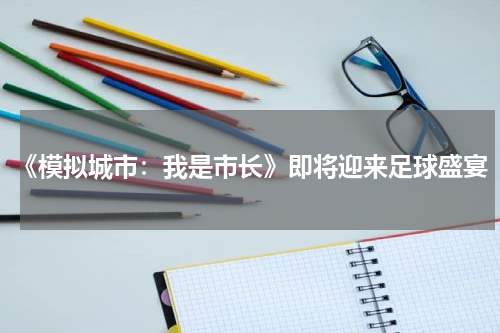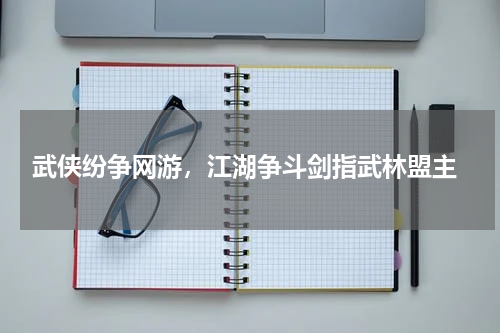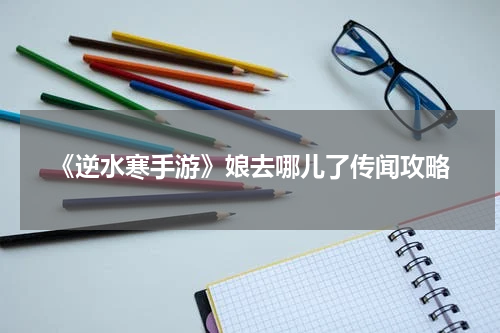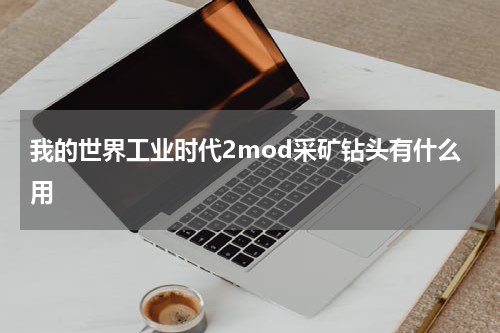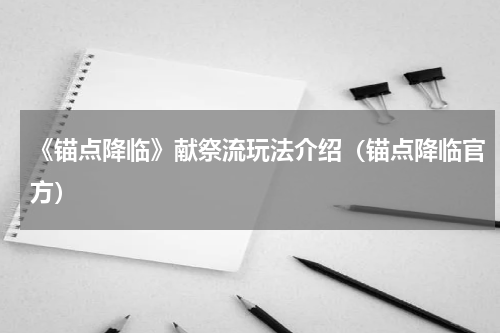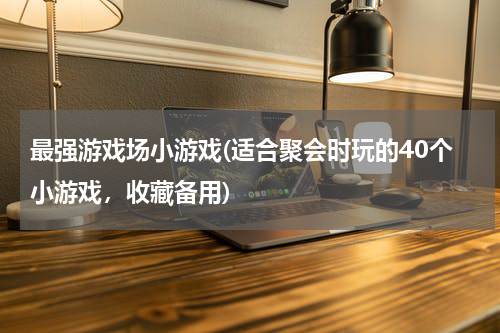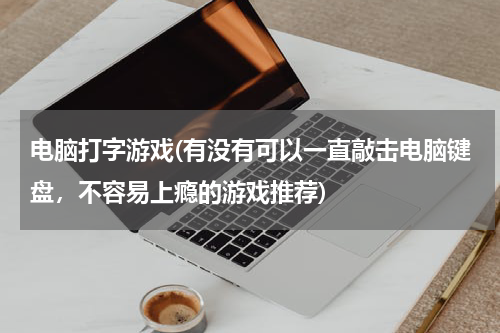所以近二十年来,在四川各地不断有关于这个“端方本”的种种传闻。端方本采用这败落的方式,当是因为归罪于宝玉。──后回宝玉的罪名不过是放纵,看来也是第一个早本的原文。端方本自娶宝钗后败落的经过用第一个早本,因此娶宝钗是原有的。旧本之二,八十回后与程本不同,但是也有抄家,因此是家境骤衰。此本也是根据这早本续书,不过将流落提前,结婚宕后,增加戏剧性。薛宝钗嫁后,以产后病死。史湘云出嫁而寡,后与宝玉结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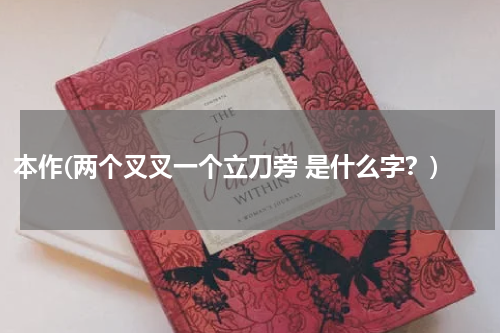
端方本的端方本流落
按照中国的说法叫 无风不起浪,既然在民间流传着这种种传闻,那么这个与一般通行本不同的 《红楼梦》抄本是否真的存在过呢?既然这个抄本是在端方处发现的 (所以称为“端方本”),那么是否有可能找到呢?很遗憾!确实如有的红学家所说,凡牵连到《红楼梦》的人和事,都有点怪。这个拥有 “端方本”的端方于一九一一年奉命入川镇压保路运动,刚到达资州,辛亥革命的风暴骤起,他就被起义的士兵所杀。 他从北京带来的几十驮架书籍和珍奇古玩亦就此失散。那个珍贵的“端方本”是否也在其中呢?
当然,如果端方入川时确把“端方本”带来了,这个抄本肯定是失落在四川无疑。所以近二十年来, 在四川各地不断有关于这个“端方本”的种种传闻。胡邦炜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过程中,也曾花费极大的力气来追寻流散于四川的“端方本”的线索,并在成、渝两地听不少人谈起过。且其中还有人说他们亲眼目睹过。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,这些目睹者文化水平并不很高,对红学亦无甚研究,但从他们口中讲出的故事梗概却基本一样,显然不是胡编乱造,故意耸人听闻。但是当笔者顺着这些线索追踪下去时,则总是要断线不是追到某一个人时他已去世,就是追到某一个人时他说告诉他的人下落不明。
因此,到底是否有过一个《端方本》,有的话,它到底是否失落在四川?这不得而知。
“三六桥本”是日本民间所流传的《红楼梦》,与“端方本”相似。详细见红楼梦魇:个五详红楼梦(6) 张爱玲 家计日落仍旧是第七十二回林之孝向贾琏说的家道艰难,需要紧缩,不过这是几年后,又更不如前了。照理续书没有不写抄没的,因为书中抄家的暗示太明显,而此本删去程本的抄家,代以什么事都没发生,又并不改成好下场,这样写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,只能是这一部份来自第一个早本。宝玉穷到无法度日,已经年长,等到老了捡煤渣,流落饥寒,也正吻合。端方本采用这败落的方式,当是因为归罪于宝玉。这是个年代较晚的抄本,迟至一九一○年左右还存在,作风接近晚清的夸张的讽刺性小说,把宝玉湘云写成最不堪的 一种名士派。但是此处写败家子宝玉只用放纵二字,轻飘而含糊得奇怪,与第三十六回王夫人口中的放纵遥相呼应──王夫人解释袭人暂不收房的原因:……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,总(纵)有放纵的事,到(倒)能听他的劝。──后回宝玉的罪名不过是放纵,看来也是第一个早本的原文。当然原本不会有拜堂阿、拨什库。端方本九十七八回后从程本过渡到第一个早本,但是受程本后四十回作者的影响,也处处点明书中人是满人,卖弄续书人自己也是满人,熟悉满洲语文风俗。
前面说过,关于第一个早本的记载模糊异常。林薛夭亡,荣宁衰替,宝玉糟糠之配实维湘云,没提宝钗嫁宝玉后才死。王伯沆引濮文?的话,更是口口声声宝玉系娶湘云,宝玉所娶系湘云,仿佛双方都是第一次结婚。难道宝钗也是未婚而死? 端方本自娶宝钗后败落的经过用第一个早本,因此娶宝钗是原有的。董康等没提,大概因为是尽人皆知的情节。至于湘云是否再醮,宝玉搞到生活无著的时候已经年纪不轻了,然后续娶湘云;湘云早先定的亲如果变卦,也不会这些年来一直待字闺中,当然原著也是写她结过婚,而且也不是小寡妇。宝玉鳏居多年,显然本来无意续弦。他们的结合比较像中年孤苦的两兄妹。连端方本也都没插入色情场面写他们旧梦重温。
旧本之二,八十回后与程本不同,但是也有抄家,因此是家境骤衰。抄没后宝玉湘云流落重逢而结合,应当年纪还轻,与第一个早本的老夫妻俩流落正相反。此本也是根据这早本续书,不过将流落提前,结婚宕后,增加戏剧性。后数十回文字,皆与今本绝异,是没参用程本,似是较早的续书。大概不会有第一个早本的原文在内──用不上。
南京刻本──哖──写宝玉作看街人,因而重逢北静王,不是重逢湘云。此点南京刻本与啕是互相排除的,并不是记载不全,顾此失彼,因为不可能先遇见湘云,然后又遇见北静王──啕写到宝玉湘云重逢后结合,全书已完;如果是先遇见北静王,那就已经转运,不做看街人了,也不会再在凄惨的情形下遇见湘云。这两个本子似是各自分别续书,而同是自然而然的将街卒木棚中过宿渲染成自任看街兵。
再来细看南京刻本的内容:画家关松房先生云:尝闻陈弢庵先生言其三十余岁时(光绪初年)曾观旧本红楼梦,与今本情节殊不同。薛宝钗嫁后,以产后病死。史湘云出嫁而寡,后与宝玉结褵。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,住堆子中。一日,北靖王舆从自街头经过,看街人未出侍候,为仆役捉出,将加棰楚,宝玉呼辩,为北靖王所闻,识其声为故人子,因延入府中。书中作者自称当时亦在府中,与宝玉同居宾馆,遂得相识,闻宝玉叙述平生,乃写成此书云云。
──扈功著“记传闻之红楼梦异本事
宝钗死于产难,湘云再醮宝玉,与端方本相同,遇北静王也大同小异,且都误作北靖王。扈功文内转述关松房听到的陈弢庵的话,两次都是口述。静误作靖显然是扈功的笔误。但是民初褚德彝记端方本事,也与近人扈功同误静为靖,未免巧合得有点不可思议。难道是周汝昌引扈、褚二文,两次都抄错了? 红楼梦新证书中错字相当多。如果不是误植,还有个可能的解释:听某某人说,也可能是书信上说的。如果扈功所引的是关松房陈弢庵信上的话,那就是南京刻本与端方本间的一个连锁。 其实这两个本子的关系用不著“北靖王作证。南京刻本把第一个早本的宿街卒木棚中渲染成自任看街兵,看街这样的贱役,清初应是只有汉人充当。端方本注重书中人是满人这一点,改为充拨什库以糊口,表示一个满人至不济也还可以当拨什库。
遇北静王一节,端方本作宝玉市苦酒羊胛,与湘云纵饮赋诗赏雪,大概宝玉醉了,适九门提督经其地,以失仪为从者所执,视之盖北靖王也。苦中作乐赏雪,与芦雪亭对照,借此刻划二人个性。但是不及南京刻本看街巧遇北静王,与职务有关,较浑成自然。
康熙三十年──一六九一年──京师城外巡捕三营、督捕、都察院、五城所管事宜交步军统领管理,换给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印信(见红楼梦新证第三五○页)。步军统领本来只管城内治安,自此兼管城外,九门提督是他的新衔。端方本内北静王现任九门提督,也是此本的润色,当代的本地风光。是端方本改南京刻本,应无疑义。 延入王府,端方本显然认为太优遇了,改为代找了个小差使:越日送入銮仪卫充云麾使,迄潦倒以终云。云麾使如果执云帚──也就是拂尘;省亲时仪仗中又有值(执)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扫尘等类,一队队过完──比扛旗伞轻便。后妃用太监,銮仪卫想必另在满人中挑选。
南京刻本末尾著书人根据宝玉口述,写成此书,这著书经过与楔子冲突,也与卷首作者自述冲突,显出另手。但是重逢北静王是否第一个早本原有的?
今本第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回、第二十四、第七十一回都有北静王。秦可卿出殡途中,北静王初次出场。风月宝鉴收入此书后,书中才有秦氏。第一个早本还没有写秦氏丧事的第十四、十五回。
第二次提起北静王,是第十六回林如海死后黛玉从扬州回来,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,被拒绝了。早本黛玉初来时已经父母双亡,后改丧母后寄居外家多年,方才丧父(见二详)。因此初名石头记时没有林如海病重,黛玉回扬州的事,当然也没有自扬州回京,与宝玉那一小场戏。
第二十四回主要是介绍贾芸,一七六○本新添的人物。贾芸初见红玉一场,又介绍红玉,早本旧有的人物。通回都是新材料,只把早本宝玉初见红玉一场用了进去,加上两句提起贾芸的对白。宝玉红玉一节这样开始:
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,见过贾母王夫人等,回至园内,换了衣服,正要洗澡。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,秋纹碧痕两个去催(炊)水,檀云(全抄本作晴雯)又因他母的生日,接了回去,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。虽还有几个作粗活听唤的丫头,估量着叫不着他们,都出去寻伙觅伴的顽去了。写此节时,晴雯的故事还与金钏儿的故事相仿佛。书名红楼梦期之前有个时期,添写金钏儿这人物,晴雯改为孤儿,因将此处的晴雯改为檀云(见三详)。所以加金钏儿时改写过此节,一七六○本将此节收入全新的第二十四回,又改写过一次。两次中有一次顺便一提北静王,免得冷落了这后添的人物。原先宝玉也许是从亲戚家回来。
前面说过,加了贾赦邢夫人迎春后,才写第七十一回。回内贾母做寿,贺客有北静王与 北静王妃。
有北静王的五回都是后添的。第一个早本没有北静王,因此结尾也不会有宝玉重逢北静王。那是南京刻本代加的好下场。
南京刻本前文应有北静王,否则无法写重逢北静王。因此南京刻本前部是今本。它也是根据第一个早本续书,而不是通部补撰传闻中的早本。
关于此本的记录,叙事层次不清,说到续娶湘云,下接宝玉曾落魄为看街人。如果是看街巧遇北静王,因祸得福后才续弦,那在湘云这方面就毫无情义可言了。但是宝玉在王府认识了著书人,想必就是同住宾馆时自述身世──包括续娶湘云的事。所以是先续弦后落魄。这也就是第一个早本的结局:宝钗产后病故,续娶湘云,后贫苦。后人复述,偏重续书杜撰的遇贵人一节,因为故事性较强,便于记忆,而原本后部是毫无变故的下坡路,没有获罪,更没有抄家──并不是略去不提。
端方本这一部份用第一个早本,只到年长时穷得过活不了,续娶湘云为止,而南京刻本一直到末了晚年流落,不过把街卒木棚中过宿加油加酱说成看街。端方本续书人手中未见得有第一个早本,大概就是参用南京刻本改写程本。
端方本改看街兵为拨什库,而看街又来自宿街口木棚中,可见原本内并没做任何工作,也没找过事。但是原本宝玉搞到过不了日子的时候,已经年纪不轻了,所以端方本此处插入找事一节,就用超龄作为不合格的理由。
湘云不识当票(第五十七回),可见社会上的事一无所知。她与宝玉一样任性,而比宝玉天真,所以是跟她在一起才终于落到绝境中。湘云精于女红,但是即使领些针线来做,也需要世故些,上门走动,会趋奉逢迎。
第一回好了歌有:金满箱,银满箱,展(转)眼乞丐人皆谤。甲戌本夹批:甄玉贾玉一干人。并没有说湘云做乞丐。讲宝玉也着重在谤字上,可能仅只是说一成了穷光蛋,人人都骂不上进。当然,这一系列批语已经不是批第一个早本了。稍前有这两句歌词:说什么粉正浓,脂正香,如何两鬓又成霜?甲戌本夹批:宝钗湘云一干人。作批的时候宝钗早卒,已经改去。
但是第一个早本内宝玉湘云再婚这样迟,然后白头偕老,纵使流落,显然并未失散了再重逢。旧本之二写湘云为丐,无非是为了使她能在风雪之夜与敲更的宝玉重逢。
因此湘云为丐与宝玉打更一样,都不是原有的。他们俩生活在社会体系外,略似现代西方的嬉痞──近来大都译为嬉皮,不免使人联想到嬉皮笑脸,其实他们并不──但是嬉痞是寄生在富裕宽容的社会上──对年轻人尤其宽容,老了也还混不下去。宝玉湘云晚景之惨,可想而知。
庚、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两则极长的批注,批宝玉续庄子的事。第二段如下:
黛玉一生是聪明所?。……阿凤是机心所?。宝钗是博知所?。湘云是自爱所?。袭人是好胜所?。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,悲亦甚矣。
黛玉太聪明了,过于敏感,自己伤身体。宝钗无所不知,无所不晓。娶了个Mrs. Knowll,不免影响夫妇感情。湘云是自爱所?,只能是指第一个早本内,再醮宝玉前,其实她并不是没有出路,可以不必去跟宝玉受苦,不过她是有所不为。
阿凤是机心所?,可见第一个早本已有凤姐,此回要角之一,更可以确定第二十二回来自最初的早本。
第三十一回袭人吐血,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,眼中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是好胜所?,是说贾家败落后,她恨宝玉不争气,以至于琵琶别抱。这条批是批第一个早本,当时已有袭人别嫁的情节,这也是一个旁证。第三十二回隐约提起的湘云袭人十年前西边暖阁夜话,同嫁一个丈夫的愿望,预言不幸言中而又不中。袭人另外嫁人,总是年轻的时候,与湘云一去一来,相隔多年,根本没有共处过。
书中用古代地名,讳言京城是北京,早本尤其严格。北京分里城外城。端方本内蒋玉菡的当铺开在外城,又是端方本特有的笔触,与此书的态度相悖。
第一个早本内袭人并没有与蒋玉菡一同奉养宝玉夫妇,因为与宝玉湘云的下场不合。袭人嫁的是否蒋玉菡,嫁后是否故事还发展下去,不得而知。蒋玉菡嫌宝玉屡次来借钱,要叫铺兵驱逐,为袭人所斥而罢,大概是端方本编出来骂宝玉的。南京刻本就没有──复述者该不会遗漏这样触目的情节。
端方本续书人鄙视宝玉,想必是因为第一个早本对宝玉的强烈的自贬。
此本还没有卷首作者自述一节,但是那段自述也写得极早。在这阶段,此书自承是自传──当然是与脂砚揉合的自画像。第一个早本的老来贫结局却完全出于想像。作者这时候还年轻,但是也许感到来日茫茫的恐怖。有些自传性的资料此本毫不掩饰,用了进去,如曹寅之女平郡王福晋,在书中也是王妃。但是避讳的要点完全隐去,非但不写抄家,甚至避免写获罪。第一个早本离抄家最远,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。
第二十一回有:谁知四儿是个聪敏乖巧不过的丫头。庚、戚本句下批注: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。作者一生为此所?,批者一生亦为此所?,于开卷凡见如此人,世人故为喜,余犯(反)抱恨。盖四字?人甚矣。被?者深感此批。末句是作者批这条批。
这位批者的口气与作者十分亲密而地位较高,是否脂砚虽然无法断定,至少我们确实知道作者自承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前引第二十二回批宝玉续庄子,批第一个早本的一条批注:黛玉一生是聪明所?。……阿凤是机心所?。宝钗是博知所?等等。黛玉太聪明了,所以过分敏感,影响健康。宝玉对于他倾慕的这些人也非常敏感脆弱。第七十回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,剑刎了尤小妹,金逝了尤二姐,气病了柳五儿,连连接接,闲愁胡恨,一重不了又一重,弄的情色若痴,言语常乱,似染怔忡之症。戚本作冷淡了柳湘莲。
第六十七回有甲乙丙丁四种,戚本此回是第六十七回乙(见四详),有许多异文,如薛蟠听说柳湘莲跟着跛足道士走了,向西北大哭了一场,可见上一回内柳湘莲是向西北方去的。那是第六十六回乙,与今本不同。还有第六十六回甲,因为甄士隐的好了歌保不定日后作强梁句旁,甲戌本批柳湘莲一干人,显然风月宝鉴初收入此书时,柳湘莲没削发出家,只悄然离京,后回再出现,已经落草为盗。根据第一个早本续书的共四种,内中大概是南京刻本流传最广,连端方本续书人这老北京也买到一部。但是予人印象最深的是旧本之二。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看胡适文存上的一篇红楼梦考证,大概也就是引续阅微草堂笔记──手边无书,可能记错了──传说有个旧时真本写湘云为丐,宝玉作更夫,雪夜重逢,结为夫妇,看了真是石破天惊,云垂海立,永远不能忘记。这位续书人改编得确是有一手,哀艳刺激传奇化,老年夫妇改为青年单身,也改得合理,因为是续八十回本,当然应有抄家,所以青年暴贫。而且二人结合已是末回卷终,并无其他的好下场,仿佛成为一对流浪的情侣,在此斩断,节拍扣得极准,于通俗中也现代化,甚至于使人有点疑惑──会不会是曹雪芹自一七五四本起改写抄没,一直难产,久久胶着之后,一度恢复续娶湘云的情节,不过移到抄家后?
第一个早本内鳏居多年后续娶孤苦无依的湘云,不能算是对不起黛玉。改为在这样悲惨的情形下意外的重逢而结合,也情有可原,似乎是不可抗拒的。但如果是曹雪芹自改,为什么要改宝玉为看街兵?在街卒木棚中过夜也尽有机会遇见乞丐。现代的嬉痞也常乞讨,而看街兵需要侍候过往官员。宝玉最憎恶官。
雪夜重逢的一幕还是别人代续的。
第一个早本源久流长,至今不绝如缕,至少有一部份保存到本世纪四○年间,而接近今本的百回红楼梦倒早已影踪全无。除了因为读者大众偏爱湘云,也是因为此本结局虽惨──与无家可归捡煤渣一比,后期的下部后数十回'寒冬噎酸虀,雪夜围破毡'不过是有些小户人家的常情──到底较有人间味,而百回红楼梦末了宝玉与贾雨村先后去青埂峰下,结在禅悟上,不免像楔子一样笔调枯淡。历来传抄中楔子被删数百字都没人理会,可见不为读者所喜。
周汝昌将第一个早本与有关无关的几种续书混为一谈,以为至少有一个异本,不过记载繁简不同,即使不是原本,也是知道原著情节,据以续补,除了做看街兵是附会,而宝玉湘云鳏寡匹配,可能是曹雪芹自己急改进呈御览,照例替内廷讨吉利。结合本来可有可无,不结合反而更主题严肃──抗议当时统治阶级的残暴,宝玉湘云抄家后都做了乞丐。
周汝昌从这大杂烩上推测八十回后的情节,又根据一道没看仔细的奏章,以为曹雪芹将发卖李煦的妇孺的事结合了他本身的经历见闻,写史家抄没时,湘云等妇女被指派或'变价'为奴为'佣';宝玉那只麒麟曾经第二次失落,被卫若兰拾了去,湘云流落入卫若兰家,见麒麟泪下,若兰问知是宝玉的表妹,骇然,大概由于冯紫英的助力,代访到宝玉下落,于是二人遂将湘云送到可以与宝玉相见之处,[按:指射圃,因为下文揣测脂砚等惧祸,抽去反抗当时统治阶级的狱神庙回与卫若兰射圃文字,所以独这两部份迷失无稿──显然认为射圃是秘密相会的地点。]撮合宝玉湘云成为患难中的夫妻(红楼梦新证第九二一页)。用两个贵公子作救星,还是阶级意识欠正确。
前面列出的旧本之五,是个八十回本,未完,写到奉元妃命金玉联姻,黛玉抑郁而死。这当然是循第二十八回的线索,回内元妃端午节赏赐的节礼独宝玉宝钗的相同,黛玉的与别的姊妹们一样。事实是这伏笔这样明显,甚至于使人疑心改去第五十八回元妃之死,是使她能够在八十回后主张这头亲事。
但是如果是这样,宝玉虽然不得不服从,心里势必怨恨,破坏了他们姊弟特别深厚的感情。如果是遗命,那就悱恻动人,更使宝玉无可如何了。
庚本第二十四回批红玉的名字:红字切绛珠,玉字则直通矣。红玉郁郁不得志,影射黛玉。黛玉怀才不遇,只能是指她不得君心。元妃代表君上。
晴雯是女儿痨死的,就必须立刻火葬。起初患感冒的时候,病中与宝玉同睡在暖阁里,麝月也怕老嬷嬷们担忧过了病气,可见从前人不是不知道传染的危险。黛玉也是肺病。子嗣的健康问题还在其次,好在有妾侍。元妃一定关心她这爱弟的健康。黛玉是贾母从小带大的,所以贾母不忍心拆散她与宝玉。元妃只见过黛玉一面。 如果不是元妃插手,贾母死后宝黛的婚事也可能有变局,第五十七回紫鹃就虑到这一层。但是这样一来,又是王夫人做恶人。这究竟不比逐晴雯,会严重的影响母子感情。
古本序读后感
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,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?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,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。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?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古本序读后感范文,仅供参考,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
古本序读后感1
王阳明先生这篇《大学古文序》写于1518年,阳明先生时年47岁,他任提督军务都御史,在江西和广东等地平定了众多叛匪,功德卓越。他一边工作,一边讲学和写作,前面分享过的《祭浰头山神文》和《教约》两文均写于此年。
《大学》原是《礼记》的第四十二篇,其著名的词句有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“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齐家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其所说的“大学”是指“大人之学”(大人即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胸襟的人)、“君子之学”(君子即责任和道义担当的道德模范者)和“仕子之学”(仕子就是心系百姓为百姓谋利的官员)。《大学》成文于战国末期和西汉之间,记载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,受到历代大儒的推崇。
后代儒学者怀疑因错简而导致《大学》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误。北宋大儒程颐和程颢先后编撰《大学》原文章节为《大学定本》。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,他认为《大学》有“阙文”(阙文指有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句),遂对《大学》“移文补传”。他认为“经”是孔子所说,由曾子所记述的;而“传”是曾子所说,门人记录的,所以就把《大学》分成了经(一章)、传(十章),为其“补格物致知传”,又把传文中对“诚意”的解释后移,置于解释“正心”之前,形成“三纲”、“八目”、“三纲释文”、“八目释文”的完整文本结构,并将《大学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合编为《四书》。后经朝廷功令,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地位突显,对后世影响很大,后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,一直沿袭到清代,成为士人应举的必读书。
自《大学》受到重视开始,对它版本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王阳明1508年在贵州龙场的时候,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。他一直伏读精思,怀疑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非圣门本旨,他认为圣人之学本来就简易明白,其书就是一篇,无经传之分,更无经可补。于是写下这篇反映他心学思想的《大学古本序》。
朱熹认为“格物致知”为《大学》之要,把“格物致知”解释为“即物而穷其理”,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`探究。在这篇《大学古本序》中王阳明说:“《大学》之要,诚意而已矣。诚意之功,格物而已矣。诚意之极,止至善而已矣。止至善之则,致知而已矣。”王阳明认为是《大学》是“诚意”为要。他把“格物致知”和“明明德”、“亲民”都解释为“正心”、“致良知”,“物格则知致、意诚”。“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,而反复其辞。”
王阳明在文中说道:《大学》“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。是故不务于诚意,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;不事于格物,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;事本于致知,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。支与虚与妄,其于至善也远矣。合之以敬而益缀,补之以传而益离。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,去分章而复旧本,傍为之什,以引其义。”他指出朱熹的《大学》改本有“支与虚与妄”之病,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。
这篇《大学古本序》和他后来讲授《大学》的记录本《大学问》都包含了他的哲学中心思想,是他心学“心即理、知行合一,致良知”思想的重要体现。他多次强调圣人之心无须外求,至善在于吾心,格物即格心,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。王阳明的讲学,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,使得王阳明对《大学》格物的认识,愈来愈清楚,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,朱熹学的权威大大削弱,《大学》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。
王阳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,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;阳明学敢于挑战朱熹等传统权威,也是一种实事求是、知行合一的体现,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;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,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、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;阳明学提倡“亲民”、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,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三个引领: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”有借鉴作用。
古本序读后感2
程颐在他的改本《伊川先生改正大学》一文中,只是于“在亲民”的“亲”字下注有“当作新”三字,尚未把“亲”直接迳改为“新”。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,并非以为有阙文,但他的“当作新”之注,确实为朱子直接改“在亲民”为“在新民”作了理论上的铺垫。朱子取程颐“亲”作“新”之意,将其解为革新、自新,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、去恶从善,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。
徐爱所辑《传习录》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“在亲民”与“在新民”之辩。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。徐爱《传习录》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,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,七月,阳明刻古本《大学》,作《古本大学傍释》,又作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紧接着八月,门人薛侃刻《传习录》,《年谱》载:“侃得徐爱所遗《传习录》一卷,序二篇,与陆澄各录一卷,刻于虔。”至此,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,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,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。先是徐日仁问道:
“在亲民”,朱子谓当作:“新民”,后章“作新民”之文,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“亲民”。亦有所据否?
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:
“作新民”之“新”,是自新之民,与“在新民”之“新”不同,此岂足为据?“作”字却与“亲”字相对,然非“新”字义,下面“治国平天下”处皆于“新’’字无发明,如云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,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,如保赤子;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,此之谓民之父母”之类,皆是“亲”字意,“亲民”犹孟子“亲亲仁民”之谓。亲之即仁之也,百姓不亲,舜使契为司徒,敬敷五教,所以亲之也。尧典“克明峻德”,便是“明明德”,以“亲九族”至“平章协和”,便是“亲民”,便是“明明德于天下”。又如孔子言“修己以安百姓”,“修己”便是“明明德”,“安百姓”便是“亲民”,说“亲民”便兼教养意,说“新民”便觉偏了。
为什么是“亲民”而非“新民”,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,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。在这段话中,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,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:
其一,“作新民”之“新”,是自新之民,与“在新民”之“新”不同,不能互为解释依据。所谓《大学章句》第三章(朱本称此章为“传之二章”)中有“汤之《盘铭》曰:‘苟曰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’《康诰》曰:‘作新民。’《诗》曰:‘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。’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”《尚书·康诰》此处“作新民”之意,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,与《大学》首章“三纲领”之“在明明德、在新民(朱熹所改)、在止于至善”之“在新民”完全不是一个意思,用“作新民”来证明所谓“在新民”的合理性,显然是站不住脚,“此岂足为据”?
其二,既然古本中的“作新民”不能用来支撑“在新民”中“新”字之改的正当性,“作”字却又与“亲”字相对,然非“新”字义,那么将“在新民”之“新”还原为“亲”则是理所当然。在阳明看来,“亲民”与“新民”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:“亲民”是惠民、养民义,而“新民”则只是单纯的教化、革新之义。阳明举《大学》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,举所谓“烈文”章“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,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”,又举所谓“齐家·治国”章“如保赤子”,所谓“治国·平天下”章“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,此之谓民之父母”等,作为自己主张“亲民”正当性的根据,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“皆是‘亲’字意”。
“亲民”与“新民”虽一字之差,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,前者于惠民、养民中爱民,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;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“亲亲仁民”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,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。如果说“亲民”与“新民”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,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,即所谓“亲民”犹孟子“亲亲仁民”之谓。亲之即仁之也,百姓不亲,舜使契为司徒,敬敷五教,所以亲之也。百姓不和睦,舜就让契担任司徒,“敬敷五教”,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。为了维护圣人之意,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更何况,“亲民”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,“说‘亲民’便兼教养意,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朱熹的“新民”说明显褊狭了。
其三,“明明德”就是“亲民”,就是“明明德于天下”。“明明德”与“亲民”本就是相辅相成的,“明明德”自然有“亲民”含于其中,无“亲民”即无所谓“明明德”,无“明明德”则哪来所谓“亲民”之存在。阳明举《尧典》说法,其说“克明俊德”就是“明明德”,“以亲九族”到“平章”、“协和”,就是“亲民”,就是“明明德于天下”,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,属圣人之意。又比如孔子说“修己以安百姓”,“修己”之“己”,是先圣所指的大人,“修己”就是“明明德”,“安百姓”就是“亲民”,己若不修,如何“安百姓”,如何“亲民”?在阳明看来,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,又岂是朱子之“新民”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?
再说,“作”与“亲”相对应,但并不是“亲”的意思,“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”,以下讲到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等处,都对“新”字没有发表阐述。
正如郑珍感叹的,由于朱子之猵狭,致使“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,亦遂争新角异,而《大学》日多矣”。郑珍于是表彰道,王阳明“复古之功不可没也”。
两个叉叉一个立刀旁 是什么字?
1、刈:yì<动>2、本作“乂”形声。从刀,乂(yì)声。本作“义”。本义:割草 3、同本义 刈,断也。又,杀也。—《广雅》 是刈是濩。—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 腰镰刈葵藿,倚杖牧鸡豚。——鲍照《代东武呤》 4、又如:刈获(收割;收获);刈熟(指收割庄稼) 5、杀 [kill] 而又刈亡之。—《国语·吴语》 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,以刈百姓。—《大戴礼记》
一个错号,一个利刀念什么字
展开全部(1)刈、yì
(2)(本作“乂”形声。从刀,乂(yì)声。本作“义”。本义:割草) (3)同本义 刈,断也。又,杀也。——《广雅》 是刈是濩。——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